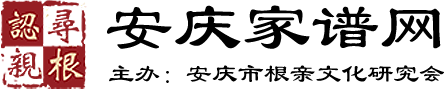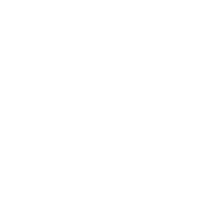食鱼随想
发布时间 : 2017-11-22 08:41 浏览量 : 25

安庆多鱼,安庆人也好吃鱼。安庆人吃鱼,全在一个“细”字上。几年前朋友乔迁新居,与几个好友一起帮忙搬家,完事后,朋友请我们在他父亲家嘬顿便饭以示犒劳,那天的菜虽然不怎么丰富,但却有道出色的菜肴豆腐鳙鱼锅让我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其汤色乳白,味香鲜美,是难以口述的。当时,我正在学厨,便带着不耻下问心情请教朋友令尊烹制之道。朋友的父亲告诉我那是他老伴的家传,不可示人。后碍于面子,拿捏了半天才吐了口。说是没有什么要领,只是当天起了个早,买了条刚上市的鲜活鳙鱼和几块顶嫩的豆腐,回家后同开两眼火灶,一眼煮几片新鲜荷叶,初沸后滤出那氤氲香水煮豆腐,另一眼将鲜活鳙鱼清煮,小半个时辰后将两者合二为一,用小火焖煮一刻,将切细的葱花点缀其间,加上盐味精便可。后来,这种做法我不知仿效多少回,可就是做不出朋友母亲做的那种味道。直至爱上写作时,才有所知,一篇同样题材文章,每个人的写法笔法就是不一样。这就同做菜一样,也是要有悟性和技巧手法的,而每个人的悟性和技巧手法有所不同,
在一家酒店当下厨时,那里面有个在日本做了20年厨的老厨师,叶落归根,晚年回故乡安庆后让酒店高薪聘请为大厨指导,动嘴不动手。这位老厨不仅手艺好,而且肚里有关食的小故事可以用节火车皮来装。有次谈到鲥鱼之味时,他说老安庆城里有一位吃鲥鱼的通家,穷数年心力,竟然生生地想出了一个绝好的解决法子。那是将鲥鱼鳞一片片活挑下,轻针细线穿了,甲衣似地披在鱼身上,和鱼一起上笼清蒸,食时用筷挑去透明的鱼鳞甲衣。这样的鲥鱼有鱼鳞之鲜美却无鱼鳞之碍口。我想,能够花这份心思煮食一条鱼的人,比起陆文夫先生在《美食家》里写的那个每日大清早起来第一桩事就是赶到朱鸿兴面馆里吃早晨刚熬好的头道骨汤下的头汤面的朱自治更是会吃。又想,这位通家估计就是您老了。而今,长江鲥鱼已经无法再去品味,估计不久的将来连刀鲚回鱼也可能会从我们的餐桌上游失。
祖父早年间在安庆城做木匠学徒,给师傅打下手,没有工钱。师傅带着几个徒弟,走东家住西家做活,幸运的话主家会贴上一顿午饭,有时主人为示敬重,上条鱼做样。这条鱼于学徒的祖父而言,纯是看货,动不得筷的。若动了,师傅当时不说什么,回去后便要饿上几餐以示对不懂规矩的徒弟惩诫,祖父和徒弟们几乎都受过如此的惩诫。一年中,只有一次可以痛快吃鱼。那是年夜饭上,师母上的最后一道菜,用二、三斤的大鱼浓油赤酱地烧了,衬上寸把长的葱条,盘在大盆里,全头全尾的端上来,这条鱼虽不是有着象征富贵意义的年年有余,而也缄藏着一种喜悦,最低是能够吃的。师傅把大盆接在手里,然后打量一下徒弟们,随后放在桌上,鱼头朝向哪个徒弟,哪徒弟过完年初一就要卷铺盖走人,意味出师了。这就好比官场上的端茶送客,不过更具市井气罢了。被指上的那个徒弟明哭暗喜给大家敬洒,大家立刻活跃起来,一边把那鱼风卷残云般剥食掉,一边想些好话儿祝福着那幸运的徒兄或徒弟。祖父吃鱼的故事多多少少含着一种以前旧生活的沧桑缩影和艰辛磨砺,每每回味,心里不禁生出酸酸的味道来,那是味觉之外的感怀和叹息。
如今,民富国裕,食鱼成了寻常事,忆往年食鱼之事,恍然大有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