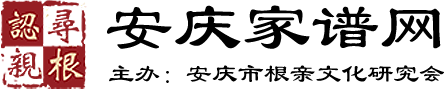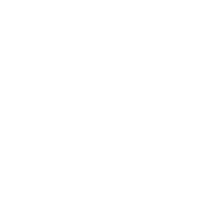“千里飘香”一碗菜
发布时间 : 2018-11-09 09:34 浏览量 : 46

在我的家乡大别山东麓,皖河的上游,那是一片丘陵地区。儿时,冬天里,下雪是再寻常不过了,雪是一场压着一场下,厚厚的积雪,如同一床巨大的棉被,把旷远的山岗和田野覆盖的严严实实。田地里,越冬的小麦和蔬菜,被捂在雪的下面,很长时间难以露头。这样寒冷的日子里,家乡人想吃一口新鲜的蔬菜,都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天再冷,乡人的日子还是暖和的。乡人善于自己给自己温暖。吃不上新鲜的蔬菜,乡人也不会为难自己。总是还有那样一碗菜,适时地出现在餐桌上,温暖着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天。
最寻常的那碗菜当是腌萝卜了。这东西家家户户都不会少储存,腌制起来很方便,都是大缸大坛的。通常是当年腌制的轮不上当年来吃,得等来年才吃。隔年吃起来反而味道更好。隔年的腌萝卜,才会熟透,通体很软很烂,无需刀切,用筷子一夹就开了,里面会有一团黑色的芯。极像是腌制过头的咸鸭蛋,蛋黄由黄色变成了黑色。而且,那种熟烂的腌萝卜,气味也很像是咸鸭蛋的气味,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臭味,但吃起来,却是别样的香味。前些年,曾经在家乡的一个小饭馆里还吃过这碗菜。不过,到了饭馆里,那碗菜就不是当年的朴实无华了,有人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千里飘香”。
不过,现在的人对于养生懂的多了,看的更重了,害怕那种不错的味道里面暗藏了一种于人有害的化学成分,不轻易再吃这碗菜了。其实,当年在村子里,常吃这碗菜的人,活到七老八十岁的,也不在少数。也许,在乡人的心目中,从来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自然,很坦荡,心中没有多少禁忌。其实,有些事情,也许真的不是书上说的那么简单,那么绝对。
当然,就算在过去,谁家也不会天天都吃这种“千里飘香”的腌萝卜的。腌制的菜,总归是咸的,吃久了不行,人会腻的。乡人自有办法给自己换换口味,另外一碗菜就会不声不响地登场了。这碗菜不再是腌制的,乡人有着自己的智慧,除了备有腌菜过冬,常常还会备有一些干菜。不合时令的干菜,在寒冷的冬天里端上了桌子,人的眼睛就会为之一亮。最常见的干菜是干豇豆、干扁豆之类。这种菜储藏起来十分简单,谁都能做。趁着旺季菜多的时候,采摘些新鲜的豇豆或者扁豆,洗净,然后下锅过水杀青,用开水将其烫成八成熟,捞起,沥干,放太阳底下晒个三两天,待其变硬变脆后,就算是干透了,可以收藏过冬了。这种干菜,怎么吃都方便。只要用水浸泡发开,煮烂了就可以吃了。单独煮了吃,原汁原味,有股甜丝丝的清香味道。若是配上些猪肉一块烹煮,味道就更加醇厚鲜美了。这种猪肉烧干菜的吃法,在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在。在合肥城里,见过好几家土菜馆,仍然有这碗菜在卖呢。
除了腌菜和干菜之外,还有一种炉子锅,也算是冬天里的当家菜了。所谓炉子锅,只是一种象形的直观说法,它是一个组合,有炉子,有锅。说的是它外在的形式,这碗菜是装在瓦锅里烧煮的,在瓦锅的下面还有一只泥巴炉子。炉子里,生有木炭火。红艳艳的炭火,从灶膛里被掏出来,放在炉子里,看起来斯斯文文毫无脾气,没有张扬的火焰,它却是挺暖人的。一只炉子锅端上了桌子,炭火不声不响,瓦锅却沉不住气了,“咕噜咕噜”地从腹底里翻腾起来,响个不停,还大口大口地喘着袅袅的热气,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不知不觉就从心里面暖和起来了。实际上,锅里的内容,比外在的形式更加暖人。那样一种简单的搭配,颜色黑白相衬,味道咸淡互抵,一锅细碎的腌菜叶子,加上两块白豆腐,放在炭火上煨煮,一种纯朴的菜香味扑面而来,就着滚烫的炉子锅吃饭,乡人三下两下就吃完了一碗饭。
这种用炉子锅腌菜烧豆腐的吃法,至今还保存着。在大别山区,冬天一到,上了年纪的乡人在家中闲来无事,总爱烧起炉子锅,就着香喷喷的咸菜煮豆腐,咪上几口老烧酒,乡人的眉眼渐渐地舒展开来。那情形,便是一种简单朴素的幸福了。
现如今,冬天已经不怎么像冬天了,雪花成了稀罕物,“溜溜子”硬是见不着了。田地里常见青绿,人家的餐桌上,菜品自然丰富多了,哪天也不愁没有新鲜的菜蔬了。在城里,更是没有过冬的概念了,生长在夏天的菜蔬,冬天一样可以吃上。可是,每到冬天,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儿时的家乡,那些冬天里的日子,冰天雪地里的那一碗菜。
那碗菜,曾经滋养着我的童年,至今还在滋养着我对一段岁月的记忆。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