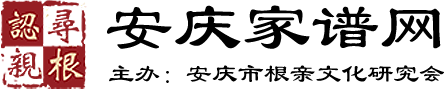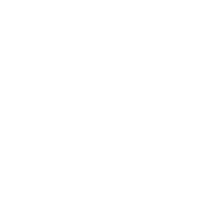糍粑香白梅
发布时间 : 2018-11-13 10:51 浏览量 : 42

那是一个中秋佳节,人月共圆时。而我因事在外,一个人呆在冷清的旅馆里,远离一切熟悉的细节。
细节看起来很淡薄,很琐小,在记忆里随时会模糊不清。但记忆里最难以忘怀的的偏是细节,尤其是那种独特的细节,特写镜头似的,深深地定格在脑海里。
对远离故乡的人来说,也是靠熟悉的细节来定位故乡。回首千万重,故乡在云端。故乡的轮廓,在心头愈来愈模糊,唯有那熟悉的细节,让故乡恒久存在,让我们在冷漠的异乡,总有一份远方的温情和呼唤。而乡愁更是一串细节组成的项链,那珠圆玉润的,是熟悉的味觉、嗅觉、视觉和听觉,或许是一份家乡的腌菜,或许是一株桂花的芬芳,或许是一片碧蓝的荷叶,或许是一曲柔情的小调,更或许是那位亲爱的人儿。
那夜,在异乡,旅馆是寂寞的温床,那一匹匹月光宛然是归乡的向导。悲伤逆流成河,我在河边,把乡愁一遍遍地反刍,满眼是家乡白梅的月下村景,回味的是白梅中秋独有的糍粑美味,那些节日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里荡漾。
在乡村,或许是纪念,或许是调剂,多年的农耕社会积累了各色的节日,还有各色的美食。白梅人的节日美食不多,三月三的米粑,五月五的粽子,腊月的晃面,这中秋佳节,不仅有香甜的月饼,还有土生土长的糍粑。家乡的节令美食,随着季节,一轮又一轮,不紧不慢地出场。
往年这个时节,秋阳还挂在独山顶上,白梅人已开始制作中秋的美食。细细听去,此起彼伏的是一阵阵捣米声,这是白梅糍粑出炉前的美妙声乐,流淌着农家自给自足的悠闲,似乎还能品味出糯米的香甜。对白梅人来说,中秋除了品尝月饼,更重要的是捣腾出一锅土色土香的糍粑。
那时,薄薄的阳光斜斜地映在室内地坪上,稻谷一般的颜色,毫无一点热力,反而微凉。秋风一起,阳光象门前的河流,看上去经年平静无波,但却真真切切地在滑动。我的女儿也拿着一根小擀面杖,兴致勃勃地捣着糯米和芝麻,随着擀面杖的一起一落,糯米和芝麻的香味在室内屋层荡漾。真是难得啊,一放假就离不了手机、无线网络的孩子,居然能丢下电子娱乐,一心参与到这传统美食的制作上,那热乎劲儿让人食欲倍增。
白梅糍粑的原料仅有两种普通的食材,糯米和黑芝麻,极简单的混合。制作也极其简单,把煮熟的糯米手工捣烂,摊平,均匀地洒上一层黑芝麻,然后切块,或长或方,可清蒸可油煎。农家的糍粑,朴素无华,远离精致,远离化妆,没有发腻的味道,口感韧实,清淡之余,还有一份土生土长的农产品的清香。
其实,多年前糍粑制作还有一道工序,是用“地宕”来捣烂糯米。地宕是本地的语言,学名叫石碓。捣糯米的,是那种两尺见方的手碓。白梅人把煮熟的糯米用纱布严密地包裹着,放进麻石制成的地宕里,同样用石头制成的锤子,一点一点地捣烂。用本地话来说,那叫“碫地”,这是个沉甸甸的活计,饱含着劳累,也饱含着庄稼人对粮食的一份虔诚。那笨拙的地宕,沉浸着岩石的味道,沧桑,厚重,还有与生俱来的地球生命的母土味道。这样制作出的糍粑,口感软滑,似乎还有一份说不清的独特的乡土风味。那时候,不用地宕制作的糍粑,那还叫白梅糍粑吗?中秋那天,白梅的村庄,都有一列在地宕前等候“碫地”的队伍。
时光飞逝,乡村已告别贫困。物质的丰盛,让我们对传统已然轻漫。对于手工制作类的精雕细琢,我们敬而远之,我们已习惯机械文明的流水线。在乡村,最典型的是手工榨油坊的消失。曾经那一座当时有点宏伟的榨油坊,已然倒塌。那石碾磨,那稻草包的菜籽饼,那些长长短短的木质器具,还有那抬着巨大撞木喊着口号的汗流浃背的赤膊汉子们,再也看不见了。
地宕还在,散落在某个农户屋后的角落里,积满了水和尘土,石锤也还在,伤痕累累,木柄早没了。偶尔,还有人想起了过去的口味,清除积灰,让地宕重见天日。只是,再也没有排队等候的队伍了。
幸好,制作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白梅糍粑那份田园牧歌式的淡香犹存。捧着一块热气腾腾的黑糍粑,品出的还是那份家的味道,清淡可口,温情脉脉。
今夜,我在清冷的旅馆,遥望家乡。
今夜,白梅一片月,万户糍粑香。